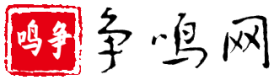今年能上春晚的网络热词里,“打工人”一定能占一席之地。
好像几个月前,大家还满口“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突然之间,每个人打招唿的方式都变成了“早安,打工人”。
不管你是不是“打工人”,这个气势磅礴的词瞬间抓住了每一只互联网弄潮鹅的心,如果你还不会玩几个“打工人”的梗,在这时尚的潮头仿佛就已经落了下风。

为什么是打工人?为什么不打老板?
紧接着“双十一”来了,“打工人”剁手之后变成了“丁工人”,“尾款人”也后来居上。每次听到那句熟悉的“加油,尾款人”,下个月的西北风都不禁让人热泪盈眶。

所以,问题来了,“打工人”怎么就火了呢?
打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即“做工”,而且多指临时性的,也就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流动性强、替代性强、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随之诞生的词还有打工妹、打工仔,意即打工的年轻女子或年轻男子。

现在我们使用了一个新词:打工人。人,无关性别、年龄,拥有一种更模煳的含义却更广阔的覆盖力,只要你和“打工”这个词能沾得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你都能在其意义域里找到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

然而,随着“打工人”被不断使用、创造新含义,围绕着这个梗产生了不少争议。当大众眼中光鲜亮丽的明星都开始自称“打工人”时, “打工人”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也随之而来。
谁可以称得上是“打工人”?对“打工人”原教旨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争上三天三夜的重要问题。
宽容地说,不拘钱多钱少、事多事少,但凡是给老板做工帮老板赚钱,自称一句“打工人”也说得过去。“打工人”的共同体验之一,就是只有辛辛苦苦干完活下班之后,才能摘掉“打工人”的标签,把老板抛在脑后,愉快地进入只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
可是,你以为你真的结束“打工”的一天,已经在愉快玩玩玩、买买买了吗?

小北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事实:你以为你在“玩”的时候,你不仅依旧是在“打工”,而且还是“打白工”。
Part 01 关于“数字劳动”的一切
要理解这件事,首先你要明白近年来在传播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哲学等学科领域越来越火的一个概念: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
这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正式出现在西方学术期刊并形成规模性讨论仅有十年。这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尽相同的解释。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数字劳动定义为:“利用身体、思想和机器三要素或组合其中两种要素作为生产工具,对于自然资源、从自然中提取的资源、以及文化与人类经验进行加工,用以生产数字媒体的劳动”。

是不是有点不明觉厉……莫慌,在深圳大学常江教授与福克斯的访谈中,福克斯更具体地介绍了“数字劳动”:
常江:您能大致介绍一下“数字劳动”具体指的是什么吗?
福克斯:在我看来,数字劳动是我们理解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基于大公司架构的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必然会受制于这些大公司的资本积累模式,因此也就必然会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劳动进行剥削。
由于互联网使用者的大部分行为——发博客、线上社交、编辑维基百科、发微博、上传视频等,都是无偿的,因此实际上这些劳动成了互联网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
这下明白多了!我们发微博、发朋友圈、发短视频甚至是点赞和评论,实际上都是在给互联网平台“打白工”。
那么,“数字劳动”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呢?换句话说,互联网平台是如何让我们给它“打白工”的呢?福克斯在访谈中也以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等)为例,进行了简单的解说。
常江:您能否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解释一下数字劳动的运行机制?
福克斯: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辩论,涉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诸多细节。在这里我们只能谈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内容。
在传统大众媒体中,我们是“受众”。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在看YouTube视频、读Facebook和推特上的帖子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名“受众”。当然,这也是受众劳工给予广告注意力的过程,也在创造价值。但我们有时也会从受众变成富有创造力的用户,可以利用用户内容生产机制,以帖子、视频、图像、评论等各种形式创造使用价值。
如果我们在目标广告平台上生产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就具有了交换价值,于是互联网平台就会出售这些数据给那些在社交媒体中投放了广告的客户。我们在目标广告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我们生产的数据商品就越多;投放给我们的目标广告就越多,我们点击这些广告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社交媒体平台价值规律的核心。
也就是说,对于今天的社交媒体平台来说,有用户就有流量,有流量就能吸引广告商,有广告商就能赚到钱,赚到钱就能活下去。我们花费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时间越多,我们生产的内容也就越多,广告商和平台也就越高兴。我们使用互联网平台,就已经是在给平台“打工”了。

Part 02我们能够避开平台的“剥削”吗?
那有人要问了,既然这样我不理它的广告,那我不就赚翻?

话是这么说没错,用互联网人熟悉的词,不能变现的流量是假流量。虽然我们为平台贡献的内容很有价值,但这些价值并不会主动转化成利润,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剥削劳动获得利润的模式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正是社交媒体金融化的核心。
但这不代表我们避开了平台的剥削。作为社交媒体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以微博为例,当然不会是卖会员,而是广告。这个交易过程中的“商品”是什么?是用户经数字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个人的、社交的元数据。
因此,认识到社交媒体数据商品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具体地说,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要投入关注,这种关注正是平台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
当然还不止,数据商品相比于受众商品有它的新特点,比如持续不断的实时监控,对意义和社会使用价值的生产,公司对于用户行为的全面掌握,产消行为(生产性消费)的出现,广告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实现设定广告空间价格的算法拍卖,等等。互联网有能力把我们的使用行为的数据搜集起来,基于此产生更多价值。
每次看到一些APP(比如x宝、x东、x多多……)推送给自己的广告,都觉得它们一定偷听了自己讲话吧!
总之,“上网冲浪”在这里不再被理解为一个我们自愿的、为了获得愉悦感的行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无偿的劳动,“自愿”被剥削。互联网平台上的每一个用户,每一个,都被精准画像而出售给广告商。

Part 03 全世界“打工人”联合起来
说到这里,我们理解的“数字劳动”大致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一系列休闲、娱乐的活动,比如刷刷微博、玩玩游戏、买买东西、追追星之类的。
加油!冲啊!不要睡!买它!
实际上,“数字劳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福克斯关注的是广义的“数字劳动”,也就是说,他不仅关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各种用户行为,还关注到整个信息通信技术行业链条上涉及的各种劳动。
具体的说,除了用户发微博、刷微博、发朋友圈、看短视频、上传视频等,生产手机的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以及996像唿吸一样自然还得经常加班的码农等等,他们的劳动都包括在内。

福克斯强调“数字劳动”是异化的劳动。他提出“三重异化”的模型来剖析“数字劳动”,指出它与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以及自身异化。
第一重异化在于我们的“自愿”。比如说,谁没有个一气之下想把微信卸载的时候呢,但是如果不去参与这种网络社交,就会受到孤立、产生社交的匮乏感,甚至直接面临很多生活出行上的障碍。也因此,即使我们知道了自己会被大平台剥削,也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接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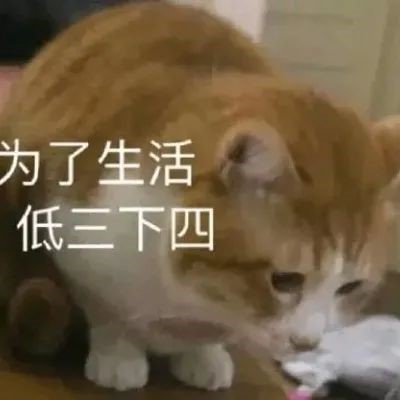
第二重异化在于我们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内容是在平台控制之下的,而平台作为生产工具属于大公司私有;第三重异化则在于劳动的“无偿”。
总之,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都被资本所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媒体生产中,不同的数字劳工遭受不同形式的异化与剥削。
福克斯还指出数字劳动的不同形式呈现全球性分布,因为数字媒体的生产、消费、储存都是跨越行业与国界进行的。他希望通过广义概念下的数字劳动,强调剥削的共性。
不过,福克斯也相信,数字媒体在加剧不同数字劳工被剥削程度的同时,也在增强这些“打工人”的团结程度,使得大家有可能在数字世界中反抗资本的剥削。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媒介更深入嵌入我们的生活,手机成为现代人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器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解媒介与传播,并以此为切口来理解当下的社会。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争鸣网]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