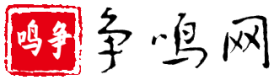亚里土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写道:“人类的贪梦是不能满足的。”它是指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这句话成了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格言,并为人类的很多经验所证实。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案修身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橡树果的兴趣。我们也已经抛弃了那些铺着草、垫着树叶的床,于是穿兽皮已经不再时髦……昨天是皮衣,今天是紫衣和金衣—这些是用怨银加重了使人类生活痛苦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将近2000年以后,列夫托尔斯素模仿着卢克莱修的说法讲到:“在从乞丐到百万富翁的男子当中寻找,1000人中你也不会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套的鞋;明天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在一所大公寓里安装一个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油画和装饰品。”
当代财富史的编史者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几十年来,继承了一笔石油财产的刘易斯·拉帕姆,一直询问人们当他们拥有多少金钱时才感到高兴。他说:“不论他们的收入怎样,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能有两倍的钱,他们将得到《独立宣言》许诺给他们的幸福水平。年收入为1.5万美元的人确信如果他每年只要收入3万美元,就会解除忧虑。年收入为100万美元的人认 为如果他每年收入200万一切就会更好了…”他总结说:“没有人曾拥有足够的金钱。”
如果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可无限扩张的,消费最终将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被经济理论忽略的逻辑结果。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令人吃惊的迹象:高消费的社会,正如奢侈生活的个人一样,消费再多也不会得到满足。消费者社会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是肤浅的。按照美元的不变价格来衡量,世界人口在1950年消费的物品以及服务就和所有前代的人消费的一样多。自从1940年,美国人自己已经使用的地球矿产资源的份额就同他们之前所有人加起来的一样多。然而这个划时代的巨大消费却也没能使消费者阶层更快乐些。例如,由芝加哥大学的国民意见研究中心39所做的常规调查表明,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人说他们现在比1957年“更高兴些”。尽管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支出两方面都接近翻番,但“更高兴些”的人口份额之比例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围绕着1/3波动。

1974年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亚人、菲律宾人、巴拿马人、南斯拉夫人、日本人、以色列人和西德人在高兴程度上都把自己列入中等行列。排除了把物质丰富和幸福相关联的任何尝试,低收入的古巴人和富裕的美国人都说他们自己比一般人幸福得多,并且印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居民较少幸福感。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所说:“在富裕和极端贫穷的国家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水平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差别。”
在收入和幸福之间存在的任何联系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幸福是建立在自己是否比他们的邻居或比他们的过去消费得更多的基础上。这样,从不同的社会,如美国、英国、以色列、巴西和印度等得出的心理资料表明:高收入阶层倾向于比中等收入阶层略幸福一点,并且最低收入阶层倾向于最不幸福。任何社会的上等阶层都比下等阶层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但是他们并不比更贫穷国家的上等阶层更满意也不比过去较不富裕国家的上等阶层更满意。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断他们自己的位置。
这个踏轮产生了一些荒谬的结果,例如,在80年代中期的娱乐场年代里,纽约许多每年“只”挣6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觉得自己很贫穷,经受着焦虑和自疑的折磨。实际上在少于60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只是跟不上琼斯家族。一个沮丧的 经纪人喟叹,“我一文不值,你明白,一文不值。因为我一年只挣25万美元,那什么都不能干,所以我什么都不是”。
从远处看,这种情绪似乎反映了纯粹的贪婪;但是从近处看,他们看起来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性,我们是需要归属的人。在消费者社会,需要被别人承认和尊重往往通过消费表现出来。正如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把“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登到《纽约时代》( New York Times)杂志上。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一个洗发水广告吹嘘说“我配得上它),又是一种社会接受的方式——世纪之交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仑所定义的“金钱体面”的一种标志。许多消费被下列认可的欲望所促动:“穿体面的衣服、开体面的车子和住在体面的生活区,全都仿佛在说“我不错,我在那个团体中。

消费满足可通过攀比或胜过他人的方式实现,也可通过好于前一年来达到。这样,个人幸福更多地是提高消费的一个函数而不是高消费本身的函数。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原因在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就变成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的奢侈品。中国工厂的年轻工人把收音机换成黑白电视一如德国的年轻经理把宝马汽车换成梅塞德斯一样真实。
在代际之间,奢侈品也变成了必需品,人们对照他们当年设立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物质舒适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满足。经过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义为贫穷。美国和欧洲贫民窟拥有的像电视机之类的东西,可能会吓坏几个世纪前的最富有的邻居,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消费者阶层对贫民区居民的蔑视,也没有减少现代穷人的艰辛感。
随着消费标准的不断提高,社会确确实实难以满足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的定义——在消费者社会处于良好地位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无止境地向上移动。父母没有购买最新的电子游戏的儿童觉得不好意思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玩;没有一辆汽车的少年会觉得和同龄人不平等。经济学家言简意赅地阐述道:“需要是被社会定义的,并且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歩提高的。消费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难以捉摸,涉及到按时间进程来比较的社会标准。然而关于幸福的研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生活中幸福的主要决定因素与消费竟然没有关系一在这些因素中最显着的是对家庭生活的满足,尤其是婚姻,接下来是对工作的满足以及对发展潜能及闲暇和友谊的满足。
在决定幸福方面,这些因素都是比收入更重要的指标。伴随着讽刺性的结果,例如,突然的发横财能使人痛苦;百万美元的中奖者通常孤立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之外,失去了从前的工作赋予他们的生活整体性和意义,并且发现他们自己甚至与亲密的朋友和家庭也疏远了。类似地斯克托夫斯基等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较高收入的人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领阶层的技巧性工作比蓝领阶层的机械性工作更有趣。经理、董事、工程师、顾问和其他的专家享有更多的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事务,因而比那些较低商业等级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的大作幸福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断定:“真正使幸福不同的生活条件是那些被三个源泉覆盖了的东西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并且在这些领域中,一种满足的实现并不绝对或相对地依赖富有。事实上,一些迹象表明社会关系,特别是在家庭和团体中的社会关系,在消费者社会中被忽略了;闲暇在消费者阶层中同样也比许多假定的状况更糟糕。”
虽然消费者社会破损的社会结构不能被测量,但在与老年人的讨论中则强烈地暴露出来。在1978年,调查者杰里米西布鲁克就他们增长财富的经历访问了许多英国工薪阶层的老年人。尽管在消费和物质舒适方面明显地得到了他们的父母和祖母们从没有期望的,但是他们更多的却是幻灭而不是满意。一位男子告诉西布鲁克,“人们不满足,可是他们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满足,我们能想象的唯一满足的机会就是比我们现在得到的更多。但是,正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东西使每个人不满足。所以如果得到比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更多时,是使我们更满足呢,还是更不满足西布鲁克访问的老年人害怕他们的孩子们,认为这一代是在物质主义世界中漂流。他们害怕摧残文化者、行凶抢劫者和强奸犯,这些人似乎残酷到他们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们感到与邻居隔离,与公众没有联系。正如他们看到的,富裕已经打破了困难时所需要的互相帮助的联系。最后,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人伴着他或她的电视机等待着他们的日子结束。
为了日复一日的生计而互相依赖那些没有到达消费者阶层的人们的一个基本特征—已一去不复返。这些联系已经由于商业大市场走进一度为家庭成员和地方企业所支配的领域而断绝了关系。消费者阶层的成员自己享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独立,然而接踵而至的便是彼此依恋的下降在美国,从50年代以来,用于邻居之间的非正式拜访、家庭闲谈和家宴的时间全都减少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年轻人认为做个好父母等同于提供许多物品。对他们来说,养育家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但是与他们的孩子共度时光却不再是生活的目标。根据艾琳克里明斯和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们的民意调查,美国中学的高年级生表达了一个强烈的“给他们的孩子以比他们曾有的更好的机遇”的愿望。但不是“与孩子们共度更多的时光”的愿望。在中学生的头脑里,“更好的机遇”显然意味着“更多的物品”。在《人口和发展评论》中写着,研究者解释说:“10年前,有谁会预见到带着设计者标签的服装和计算机游戏将会是一个幸福儿童的必要投入?
经过上一个世纪,大市场已经接替了大量的一度由家庭内部提供的生产任务,减少了人们实际上的互相依赖。金钱越来越充足,时间越来越少,我们选择了精美的包装食品、神奇的清洁用品和一次性使用的从餐巾到相机的各种方便的东西。
家庭经济的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消费者阶层的妇女把她们自己从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男人们没有去填补这个空缺,而是将家务劳动转移到市场,从妇女新的工作收入中支付。由于男人和女人都走出了家庭,破坏了家庭经济,家务劳动被迫转轨到金钱经济。家务劳动中的两性不平等仍然存在,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就是随着家庭从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单位转变到一个被动的消费体,妇女的全部工作负担已经加重了。美国妇女在60年代初,例如,尽管有许多“节省力气”的机器,她们仍然做着和她们的父母在20年代所做的一样多时间的家务。并且平均说来,美国妇女自从1965年已经减少了一点家务工作的时候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家庭外45从事着工作。同时,自从1965年起,美国男人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竟几乎没有增长。来自英国的数据也说明了一个类似的趋势。
家庭经济的商业化已经使自然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家庭中转移出来的家务杂事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完成。如在商业机构熨洗衬衫需要两个来回,通常是用汽车送到洗衣店,再从洗衣店送还给客户;从餐馆带回的肉食或用于养育一个家庭的冷冻食品切片成倍地增加了包装材料和运输能量。

在消费者社会的理想家庭中,人们几乎不为自己做事。我们不用从生食开始烹调我们的食品(55%的美国消费者的食品预算花在了餐馆的饭菜和即食的方便食品上)。我们既不缝补也不熨烫更不制作我们的衣服;我们既不用烘烤也不用建造更不用我们自己修理;我们除了孩子几乎什么也不生产,并且一旦我们做了那些事,我们就降低了身价。照看小孩的日托制比旧式的、现已消失的大家庭更加方便。一次性的尿布(典型地,第一年的3000块,花费570美元)已经代替了布片。
家庭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演变在富裕国家的住房设计中体现得很明显。老式的房子有食品室、工作间、缝纫间、嵌入式衣柜和洗衣槽。新家庭只有简单得不过装有加热精制食品设备的厨房。洗衣间和储藏块茎植物的地窖让位于热浴缸和家庭娱乐中心。基本的工作间压缩为多用途的卫生间。为弹子房和4大屏幕电视让出空间。甚至园艺,一种仍然在消费阶层流行的家务生产的形式,也正在慢慢地变成一种消费形式,如用购买物更新后院的资源。例如,英国人1991年在他们的花园和草皮上大约花费了30亿美元,而10年前是10亿美元。
人像家务劳动一样,在金钱经济的盲目作用下,公共经济也已经萎缩——或者被肢解。购物街、高速公路和“连锁店”已经取代了街头商店、当地餐馆和露天剧场有助于在一个地区创造一种一致性和社会性感觉的东西。传统的社区在一些国家几乎消失了。在美国,地方经济消亡的地方是最先进的地区,许多邻里关系不过就是共在屋檐下而已,邻居只是共有一个电视租借特权和一个便民店的地方。平均说来,美国人每五年搬一次家,并且几乎不和住在他们附近的人发展友好关系。
零售业的转变是全球消费者社会中传统社区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英国研究者卡尔·加德纳和朱利亚·塞泼德描述了随着地方零售业的衰落,从而城市和集体的认同丧失的过程.“市镇中心,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自然中心……已经失去了它的个性和与非凡过去的任何联系。现在它只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许多人的一个无个性的形式。在购物时间之外…作为零售一元文化的结果,许多镇子和城市的中心已经变成了封闭的、枯燥的、无生命的空间。”
消费者社会的人们所付出的另一个代价似乎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测定了六个国家的人们在街道上的平均步行速度和邮局职员的平均说话速度,结果表明生活节奏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增大而加快。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增长得最快,接下来是美国人、英国人、台湾人和意大利人,印度尼西亚人在六个国家的人中是走得最慢的。换句话说,随着国家变得富裕,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着急。
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定律表达了1978年的研究结果:“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人们越重视时间——因而越绞尽脑汁去节省它——人们就越不可能放松和享有它。闲暇时间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不能在空闲上“浪费”,并且,甚至锻炼身体也变成了浪费的一种形式。在1989年,美国人把10亿个工作时的工资用于购买像日球-莱克拉(Day-Glo- Lycra)一样的紧身运动服、风道检验的自行车鞋和用太空时代的聚合物编织成的防雨夹克衫。作为劳动报酬的休闲穿着已经代替了休闲。同时,在日本,一种被称为reja buma的休闲吊杆已经和正在兴起的关心自然——加速了英国进口的高耗油的、四轮驱动的漫游车(Range Rovers)和由美国进口木料制造的小屋的销售—结合在一起。
尽管同行业的工会会员在上一个世纪里已经赢得了工作时间的缩短,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工作时间仍然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平均工作时间。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蒙特利尔的麦古48尔大学研究闲暇的一位建筑学教授注意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节日将工作年的时间减少到刚好低于2000小时的现代水平。
消费者社会不能兑现它的通过物质舒适而达到满足的诺言,因为人类的欲望是不能被满足的。人类的需要在整个社会中是有限的,并且真正个人幸福的源泉是另外的东西。事实上,社会关系的强度和闲暇的质量—二者才是生活中幸福的决定性心理因素——似乎在消费者阶层中减少的比提高的多。消费者社会,似乎是通过提高我们的收入而使我们陷于穷困的。(完)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争鸣网]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